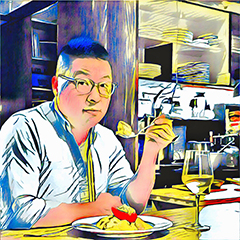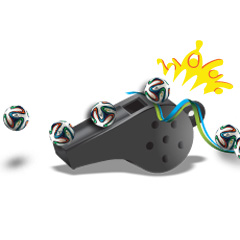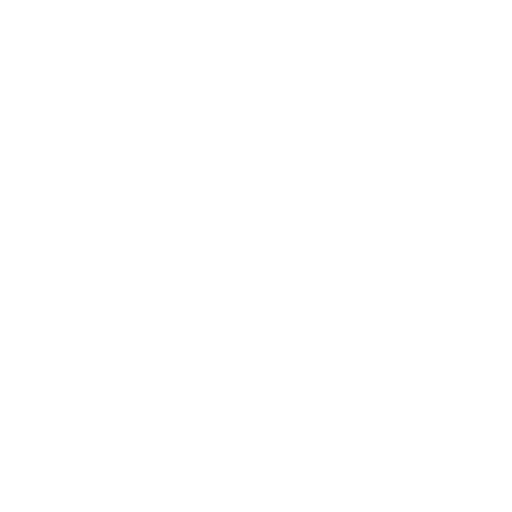21/10/2009
身份是有意思的東西
在我們身上,至少有兩種身份,一種是別人看見的,一種是自己知道的。每人都擁有外在和內在兩種身份,於是在人家當你是什麼人的時候,你又會知道,其實自己是什麼人。
如以籍貫而論,就像最近我在青島旅行,碰到幾個朋友,我當然以為他們都是青島人,但一說起來,他們就會自報家門:我是濟南的;我是煙台的;我是曲阜的。
於是我就笑:好了,好了,都是山東人。
他們則會覺得,我這種分法,粗疏了一點。
所以說,地方主義是消滅不了的,人們太自在於自己的籍貫身份,不管這個身份是貴是賤——有些大地方的人生怕人家不知道,有些小地方的人生怕人家知道——但卻跟烙印一樣,烙上了,就隨身了。
我在上海生活了22年,然後又在香港,至今已經30年,我酷愛這個城市,所以我覺得自己是香港人,大部分內地朋友,也都認為我是香港人。但很奇怪的是,大部分的香港朋友,認為我是上海人;大部分的上海朋友,也認為我是上海人。
香港朋友覺得我是上海人,是因為他們覺得我身上有些與他們相異的東西;同理,上海朋友因為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些與他們相類的東西,便一口咬定我是上海人。
這其實是很好玩的一件事,說明「身份」真的很難「洗刷」,於是我也學習踩在一條分界線上,看著兩邊都熟悉的人事,看著他們互相之間的隔閡,心中卻有洞若觀火的優越之勢。
這就讓我想起了一些舊事,下一次,用這些舊事來解釋一下這個專欄的名字,為什麼要叫「羅湖橋兩邊」。
那是金庸先生說過的一件事。
當年他從內地到香港,從深圳過關,經羅湖橋,向香港那一邊過去。那時羅湖橋十分簡陋,橋面鋪著漏著縫隙的模板。還未到橋中央,一個人從橋邊突然跳出來,一把搶走了他的手錶,扭頭逃之夭夭。
金庸先生就如此,在將到未到香港的時候,丟了自己的手錶。
聽完這個故事的時候,我也努力去回憶當年自己從深圳過香港經過羅湖橋的情景。大概沒有人從橋邊跳出來搶過我什麼東西,所以想了半天,都想不出那天是如何過橋的。
記得最清楚的,反而是當年簡陋的深圳邊防檢查站,一間簡陋的屋子裡,有一張簡陋的高桌,高桌後站著兩個邊防官員。過關的人把通行證遞上去,他們一個拿起看看,交給另一個,那一個把手上的大印沾一下紅色的印泥,啪,蓋好了,你就可以走了。
我那天過關是在正午時分,拿著蓋了印的通行證,經過那張高桌,後面就是一道像美國西部地方酒吧那樣的木門,上空下空,兩扇門只攔在中間,雙手分推,一下子打開,人就到了塞外。二月的陽光很猛烈,把腳前一條洋灰路照得發白,使剛走出屋子的人眼一花。我就如此眼花花走上那條白路,知道前面就是香港,但看不清香港是什麼模樣。
有趣的是,在以後的日子裡,我的身份,注定了我時時會站在這一條界線上,同時看著兩邊,有時也會幫兩邊的朋友溝通,幫他們溝通的時候,我就想起羅湖橋,覺得自己也有像這條橋。
《經濟通》所刊的署名及/或不署名文章,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,並不代表《經濟通》立場,《經濟通》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自由言論平台。
樂本健【年度感謝祭】維柏健及natural Factors全線2件7折► 了解詳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