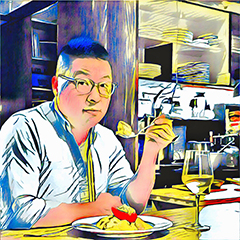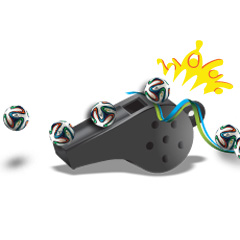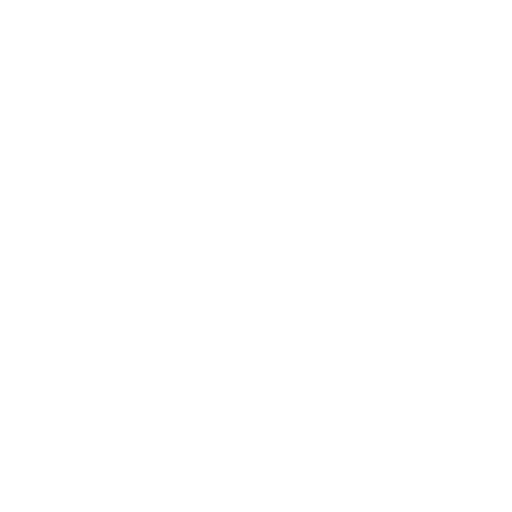16/10/2019
當希望變得沉重:如何在精神復元路上賦權
精神復元運動自美國80年代尾興起,後傳至英國澳洲等地,近年香港也出現以復元模式發展的服務。運動起源於服務使用者對生物醫學模式主導的精神科不滿,當被判斷患上精神病,也隨即被告知其病徵會伴隨一世,不要對餘下的人生抱有期望。復元運動推動者指出,即使是被視為重症的精神分裂也有復元的例子。復元路上病情可能反覆,但服務使用者也有權利活出有意義的人生,不受歧視。他們強調自主性,選擇自己的復原路,走出自己的人生。故此,「希望」被視為復元模式其中一個主要原數,為服務使用者賦權。
怎樣為服務使用者帶來希望?灌輸正向思維有時會適得其反。有研究指出希望可令人更脆弱,因為你所希望的不一定能達到,反過來會增加失望感。例如一個基層服務使用者,即使他精神狀態穩定、渴望工作,面對學歷歧視和殘疾歧視,他面對的是比其他人少的工作機會。即使有主觀盼望,但沒有客觀機會配合,希望也會幻滅。
那麼,面對病情反覆和各種歧視,如何在復元路上匍匐前進?筆者曾在英國訪問當地華人,了解他們的復元歷程,以及他們對未來的願望和想像(註1)。我發現希望不一定帶來賦權。訪問者的回應大致分為三類。第一類受訪者清晰表達他們的願望。軒少年時被診斷罹患精神分裂,現在已復元,也不擔心病發,因為她找到宗教信仰的支持,讓她充滿希望。令她耿耿於懷的,倒是家人經常提起她的住院經歷。是基督徒的身份認同,令她有信心做一個「新的人」,與精神病史說再見。玲也能說出她的希望,但與軒相反,這願望卻讓她陷入失望的循環。玲喜歡看電視台的模特兒選秀節目,看到五光十色的舞台和閃耀靚衫,覺得人生有希望。於是她買名牌衣服,但失業的她因此欠下債務。為螢幕上纖瘦的模特兒著迷,也同時感慨自己除了身上肥肉便一無所有。消費主義和媒體造就普羅大眾對上流社會生活的嚮往,在階級分明的社會下,這種希望卻加深了低下階層的攀比和焦慮。
第二類受訪者談希望時比較小心翼翼。他們謹慎,是為了避免希望落空時會失落。美說如能完全復元,她想能自己開車暢遊英國,不用怕恐慌發作。但她強調「不敢希望」,因為即使安排好一星期的計劃,也可能因病發而不能如願完成。對美來說,希望很沉重。她覺得醫生也放棄她了,只叫她試不同的藥。所以「不敢希望」是一種保護機制。那她怎樣看自己復元的進度?當恐慌發作或情緒突然低潮,第二天她會問先生「我病發得好嗎?我有沒有亂罵你們?」當先生說她處理得很好,她就知道自己有進步。所以她以「病發得好」來面對反覆的病情,掌控自己的復元歷程。第三類受訪者迴避談希望。峰給我的感覺是不想想像未來。他在英國申請庇護,他在中國餐館工作,即使工作環境惡劣令他患上精神病入院,出院後也沒有其他選擇,不讀英語也沒有學歷,只能回到餐館去。他怕工友看穿自己有精神問題,於是自己困住,不同人溝通。但當聊到當初為甚麼去英國,他想起自己不想困在鄉下漁村,他想見識大世界,有很多東西想學想看。雖然他逃避談希望,在與他回想人生觀的過程中,他流露了想自主人生的渴望。
由受訪者的經驗可見,有時希望並不一定有利復元。促進服務使用者的自主性,可幫助他們在復元路上前進。個人方面,如優勢觀點主張服務焦點不在病理或個人不足,而是他的優點。要尊重服務使用者的自主性,看見他們在自身長期面對精神困擾也能發展自己的一套韌性。社會方面,要正視限制自主性的結構因素,如階級差異所帶來的焦慮、剝削的工作環境、和對精神病者的歧視,才能為復元創造有利的社會條件。
註1:Tang, L. (2019) Recovery, hope and agency: The meaning of hope amongst Chinese users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the UK.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, 29(2), 282-299.
《經濟通》所刊的署名及/或不署名文章,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,並不代表《經濟通》立場,《經濟通》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自由言論平台。
【與拍賣官看藝術】畢加索的市場潛能有多強?亞洲收藏家如何從新角度鑑賞?► 即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