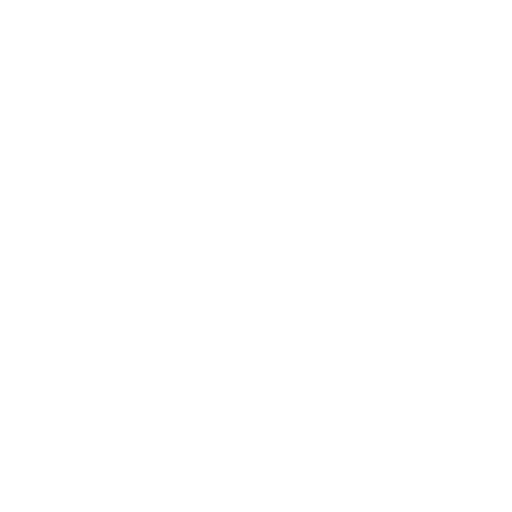10/03/2022
展覽「自我認知的三重路徑:如是我行」生命存在著各種的二元對立,人們都只是在兩者之間流離
林靖風 Cyrus Lamprecht
林靖風 Cyrus Lamprecht
荒謬主義作家及TEDx講者、Central Saint Martins藝術理論及哲學系研究碩士,曾在倫敦Tate Modern及亞洲各地藝術展覽展出多媒體(雕塑、裝置、表演及攝影)作品,創作主題圍繞於孤獨與存在的命題。近期散文、小說及詩詞作品散見於「*CUP」、「虛詞」及「好集慣」等文學平台。
Instagram:@cyrus_lamprecht夢囈之上
隔週四更新

邁克爾・穆勒「自我認知的三重路徑 ― 第四章:如是我行」。圖片來源:世界畫廊。
或許人們自出生以來,就只有一個迫切的問題需要解決,那就是如何成為一個人。皇后樂團(Queen)的歌曲「譏諷」(Innuendo)中,主唱佛萊迪·墨裘瑞(Freddie Mercury)以高吭的嗓音吟唱著:「你可以變成你所想要成為的一切,就讓自己蛻變為你所能成為的所有。」(You can be anything you want to be. Just turn yourself into anything you think that you could ever be.)在大多的時候,我們都只可以成為別人所想像的自己。倘若有著真正的自我,也許早已在成長的路上蕩然無存。世界畫廊(Galerie du Monde)帶來藝術家邁克爾·穆勒(Michael Müller)個人展覽「自我認知的三重路徑」(Drei biographische Versuche)的第四章「如是我行」(Das gemachte Ich),以一系列帶有象徵元素的裝置、雕塑、繪畫及影像作品,讓觀賞者窺探他對於存在與身分認同的反思。
空罐子與牛奶

邁克爾・穆勒「自我認知的三重路徑 ― 第二章:觀雲識天」(左)及「自我認知的三重路徑 ― 第一章:見微知著」(右)。圖片來源:世界畫廊。
經過了首兩個章節的展覽,穆勒略過了本來預定為一場表演的第三章,來到了第四章的「如是我行」。對比之前以方格紙與黑色地板作為佈置的前兩個章節,這一次的展覽以漆上明黃色的牆壁交織於一個全白色的空間;彷彿穆勒想要透過最後一章的展覽回歸簡樸的探索,讓本來可以用作定位的方格紙回復為一張屬於自由主義哲學家約翰·洛克(John Locke)的白紙一般。展覽主要可以劃分為兩個部分:明黃色的牆身象徵著一種形而上與對於個人身分的探討、白色的區域則是針對物質與集體意識上的議題。

邁克爾・穆勒作品「假印度人」(Falscher Inder)(2015年)。
位於帶有一個引號標記的黃色牆壁前的作品「假印度人」(Falscher Inder),以兩根大理石柱及鮮牛奶,重塑印度教寺廟中對最高神濕婆(Shiva)進行敬拜的儀式。印度詩人泰戈爾(Rabindranath Tagore)曾在「園丁集」(The Gardener)中寫下:「在池塘邊陲那道屬於濕婆神廟的大門打開了,敬拜者開始誦經起來。你把一個容器放在大腿上擠壓著牛奶。我提著空的罐子佇立著。我並沒有靠近你。」(On the side of the pond the gate of Shiva’s temple was opened and the worshipper had begun his chants. With the vessel on your lap you were milking the cow. I stood with my empty can. I did not come near you.)
擁有四份之一印度血統的穆勒,以西方的設計去塑造兩根屬於東方宗教的石柱,而當中所使用的鮮牛奶亦為香港本地的出產,在各種文化背景之間穿梭。創作這一件作品的穆勒會否就是泰戈爾詩作中的「我」?在於身分認同的命題上,我們或許也只是提著一個空罐子,等待牛奶一天自己會竄進容器內,卻不敢主動地靠近。不論是個人或是更高的存在,這一種欲言又止的想法,只會讓自己越走越遠。或許這亦同時反映於穆勒決定引號標記的長短程度:白牆上的引號只有黃色牆壁上的標記約四份之一的長度,似是象徵著穆勒與自我所相隔的距離。
本體的消失

邁克爾・穆勒作品「一天的工作」(Tageswerk)(左,2015年)及「自己動手做」(Mach dich selbst [Do-it-Yourself])(右,2015年)。圖片來源:世界畫廊。
穆勒在白牆前的空間內,置放著兩件帶有現象學(Phenomenology)意象的創作,由378件粘土所組成的陶瓷作品「一天的工作」(Tageswerk)及黑白影片「自己動手做」(Mach dich selbst [Do-it-Yourself])。法國哲學家莫里斯·梅洛—龐蒂(Maurice Merleau-Ponty)在著作「知覺現象學」(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)中論述:「身體並不屬於外在事物之外,它一直都特有地存在於外在之中。」(The body therefore is not one more among external objects, with the peculiarity of always being there.)
人們窮盡一生去釐清自己與物件的關係,卻意識不到在產生想要「擁有」的慾望的時候,自己其實就與物件無異。「一天的工作」裏的378件粘土作品,都是穆勒親手在瞬間捏製而成的。當觀賞者拾起附有穆勒手印的粘土的時候,其中一方定必會失去自己的存在。若當下所感受到的是穆勒的手印,粘土的本體就會隨之消失。若觀賞者所接觸的只是粘土的形狀,穆勒的捏製過程亦再不存在。在穆勒的黑白影像作品「自己動手做」內,他以兩手反覆做出一系列纏結與鬆綁的動作。在現象學的前提下,當左手或是右手主動去觸碰另一隻手的時候,原來的手會否因而泯滅了自身的存在?
何處惹塵埃

邁克爾・穆勒作品「Aatmasamarpan Mudra」(左上,2021年)、「Saindakraipe Mudra」(右上,2021年)及「Eegal Ving Mudra」(中下,2021年)。圖片來源:世界畫廊。
穆勒的三張鉛筆素描以宛如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處死時的手勢,展示在觀賞者的眼前;然而在畫作的命名上如「Aatmasamarpan Mudra」、「Saindakraipe Mudra」及「Eegal Ving Mudra」釐清了作品的主題是為印度傳統手勢的象徵。馬塞爾·杜尚(Marcel Duchamp)的達達主義(Dadaism)及雅克·德希達(Jacques Derrida)的解構主義(Post-structuralism)都娓娓地論述著觀賞與詮釋之間的差異。從來符號與手勢所涵蘊的意義,都需要根據一個人自身的文化背景,才可以作出準確的詮釋。圖像的本身其實並不存在著任何意義,但是人們就是需要為各種事物貼上一個明確的標籤,目的是為著否定「本來無一物」這一個概念。

邁克爾・穆勒「自我認知的三重路徑 ― 第四章:如是我行」。圖片來源:世界畫廊。
在於視覺的表達上,首先吸引觀賞者的兩組作品或許會是「你能教我如何戰鬥嗎?」(Can you teach me how to fight?)及「主題圖案之九(雙標題)」(Motivbild Nr. 9 [zwei Tite])的油畫及裝置作品,因為它們都存在著對於私處的仔細描繪。這兩組作品會被觀賞者以偷窺的形式來欣賞,因為他們所身處的是一個公共空間,自然就不可以展露自己最原始的慾望。
人們從來沒有真正看過男性下體上的那些嶙峋血管,亦沒有留意到女性雙腿之間的疙瘩。他們心中的慾望與自己的行動互相違背,這一種內心的掙扎貫連於穆勒的展覽之中。生命存在著各種的二元對立,人們都只是在兩者之間流離。我們希望可以找到一個永恆的解決方法,但最後或許只會發現原來一切都只是荒謬的存在。就如英國喜劇劇團「踎低噴飯」(Monty Python)在電影「萬世魔星」(Monty Python’s Life of Brian)中說道:「所以總該看看死亡那光明的一面!」(So 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death!)因為我們身處於一個虛無的時代,所以擁有希望就是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。希望建基於絕望之上,在沒有退路的時候,就只可以繼續往前走。
邁克爾・穆勒 —— 「自我認知的三重路徑」第四章:如是我行
日期:即日至 2022 年 4 月 2 日
時間:10:00 – 19:00
地點:世界畫廊 Galerie du Monde 中環都爹利街11號律敦治中心108號
觀展須知:展覽目前只接受預約參觀,每節時段最多兩個名額。展覽內容兒童不宜,設有年齡限制,年滿18歲以上人士方可入場。
查詢:世界畫廊
參考文獻
Merleau-Ponty, M. (1962).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(1st ed., p. 105) (C. Smith, Trans.). London: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.
Monty Python. (1979). 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. On Monty Python's Life of Brian. Virgin Records.
Queen. (1991). Innuendo [Song]. On Innuendo. Parlophone.
Tagore, R. (1913). The Gardener (1st ed., pp. 30-31). New York: The Macmillan Company.
《經濟通》所刊的署名及/或不署名文章,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,並不代表《經濟通》立場,《經濟通》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自由言論平台。
【etnet 30周年】多重慶祝活動一浪接一浪,好禮連環賞! ► 即睇詳情